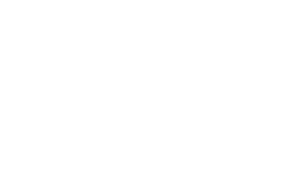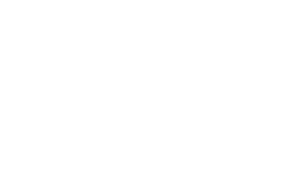我至今记得2012年春节,门前一地的鞭炮炸成一团团血色“花儿″,而我父亲忽然从口里吐出几团血,正好压在细碎的鞭炮屑上。 县医院治不好,就去武汉同济医院。在同济,住了几天。当父亲看到每天高额费用,当他听到实习生说他病情不一般,而且估计得终生离不开医院时,脸色一沉,立马自己取了针,嚷着不住院了。他大呼小叫:“我老大两孩读书,老二的儿子自小患重病,每年的药费达几万。把我治好,他们不就垮了?我活了六十几,死也死得。” 父亲一生牛脾气,犟,说出的话如泼出去的水,无论我们怎么做工作,九头牛也拉不回。没办法,开了些药,我们悻悻离去。但透过后视镜,我依然看到面色凝重的父亲隐隐含着忧伤和无奈。 六月份,父亲病疾加深,生命垂危。县里医生摇头:“拖回去吧,还有一口气…” 我不相信父亲会离开我们的。父亲年轻时多健壮,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。曾经他一双手能把石滚举起;一条“冲担”挑起四捆稻谷;农忙时,他起五更睡半夜劳作也不累;农闲时,他烧土窑里的泥瓦,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,大火熏得满脸漆黑,只有血红的眼睛能让人看得见他。 那时候,我在外地,不断地打医生的电话,医生最后建议就近去长江那边的黄石,医生联系了救护车。而那个时候,老家亲戚已自发帮我们张罗父亲后事,订好了棺材寿衣,也邀约好锣鼓唢呐热闹的班子。 我是天黑时急匆匆赶到黄石。父亲全身插满了管子,心电图仪器在他身边一直闪烁着幽蓝神秘的光芒。我和母亲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,两眼死死盯着心电图,害怕风吹草动,害怕他三长两短。夜半时分,父亲醒来,他颤抖地摸着我和母亲的手,眼睛渗出泪花。 黄石医生救了父亲的命。“老人家,您是尿毒症,不是什么要生要死的病。就是在您手上造个“瘘”,每周透析两三次,把血中的毒滤掉。您也不必担心高额医疗费,国家政策好,大部分给您报销,相信小部分您儿子有那个能力出,他们又不是不会挣钱?不治,那叫错死!冤死!” 母亲千恩万谢,我破涕为笑,父亲欣然点头,而父亲何尝不曾有过求生的希望? 直到第二年下半年,父亲终于从黄石转院到县中医院就近透析。多好,一方面解决了父母亲路途遥远的舟车劳顿,另一方面,更加充分地享受医保政策,减缓了家庭经济压力。 父亲一生脾气不好,声音大,人又犟。母亲常常笑着说:“像头牛,不开化(较真)。” 譬如他要喝水,声音很大,“端水来”。旁人一不小心,吓了一跳。母亲就端来水。他又吼,“太烫了”。母亲就用嘴巴吹一会,凉了。譬如,透析完,人有些虚脱,不能动,但要上卫生间,而母亲刚好去微波炉加热他要吃的饭菜,不在他身边。父亲就瞪着眼睛喊:“死哪去了?我要上厕所。”远远听到吼声的母亲一路小跑过来。旁边病友看不下去,说:“这人要不得,病就病了,还像个皇帝”。母亲则乐呵呵地向那人摆手,她怕伤着父亲的“玻璃心”。 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几十年,母亲太了解父亲,母亲从不把父亲的吼呀喊呀放进心里去。母亲最多说:“像牛,不讲理。”其实,别看父亲颐指气使,耀武扬威,不过就是纸老虎,家中大事小事还得听母亲,父亲从没向母亲扬过拳头。 有一次,母亲带父亲去透析,不知为何父亲有些烦躁,口里嘀嘀咕咕、骂骂咧咧。母亲笑着说:“又'牛'起来了?再骂,把你这老家伙推下岸去,免得我一辈子为你劳心费力。” 父亲叹气说,“你舍得推?要是坠下去多好,一了百了,免得折磨你。对不起…”父亲说着说着伤感起来,眼睛泛起泪光。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。走近,扶着父亲,继续走着那人生曲折坎坷的路。 父亲是永远离不开母亲的。大集体时代,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。那时活重,吃不饱。每遇工地加餐改善伙食,父亲舍不得多吃,就打好包,揣在身上,连夜走十几里山路送回给母亲,第二天鸡叫五更起床,披着霜露赶往工地。田地承包到户时,很多人忙完春种秋收,就去城里做工,而父亲不,日日里背着个“檀树弯弓",拎着木锤、纺线竹子车,挨家挨户给结婚出嫁人家弹棉花、置新絮。收工回家,踩着月光和母亲一道给油菜苗浇水给菜园扯杂草。后来,即使去外地,也顶多十天半个月回一趟家。母亲说:“念家”。 父亲身患尿毒病已经多年,而照顾父亲寻医问药及吃喝起居全然落在母亲身上。我们不忍心,希望请人分担,但父母亲异口同声:“不需要,即便请别人,也不放心。”父亲住院的日子里,母亲要么在床边支个帆布小床,要么和父亲一起挤在病床之上。 某一天,我放假,替换母亲。在医院八楼上,父亲挪到窗前,挺直站立,目光一刻不停地注视窗外。我疑惑。父亲手指医院大门,“你看,你母亲快出医院了。你看,你母亲是不是老得很快?”我开玩笑:“您也真是,老娘不是天天在您身边,才走一会,你就舍不得?”父亲没有回答。我看他一直用目光把母亲送到金秋的风中送到苍茫的人海中。 这些年,我们兄弟和姐姐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,回乡屈指可数。唯有长假,唯有春节,才短暂地接过母亲的"衣钵"。只有这段时间,我才能和弟弟轮番接送父亲透析。每年初一,我们不是先去走亲访友,而是和父亲一起去医院。记得有一次,天还在黑暗之中,弟弟跑过来敲我家门,老头老娘不见了。我想他们肯定去医院了。遂打电话,果然父母在去医院的路上。他们不想我们大年初一开车送他们。 天黑伸手不见五指,我启动车子,打开雾灯,循着他们必经之路去追。在大雾里,父亲借着手电筒的亮光,吃力前行。而这时,身后弟弟的车子响着喇叭赶来。 父亲责怪我们不该来。他说,以前去县里赶集,身上挑着一两百斤的猪崽,不也是走了三十多里?母亲说年年大年初一让你们送,心里有愧。 那天凌晨,我们四个人索性开两辆车子,冲破重重迷雾和幽暗,在曙光降临时,赶到县中医院透析楼。 2016年年底,父亲每况愈下,骨折,中风,又是肺癌,辗转多家医院。 2017年那个秋天,也是父亲最后一个秋天,我携孩子赶往医院探视。那时,父亲尚且能动,但手边要有拐杖和轮椅。父亲忧伤地看着我们,甚至是哭。他哽咽地说:“我怕是看不到孙女出嫁、孙儿结婚的那一天。好世界,没看够…” 那时候,我悲哀地看到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父亲,像被吸干了水,干枯、瘦小、弯曲,如同晾晒多年的一把柴。那日,我执意要用手去按摩父亲的双脚。那双脚像两根枯竹竿,破损、干裂,只剩下褐色的皮。近来,又一直麻木酸痛。 “没事的。”在父亲缩过双腿的刹那,我紧紧抓住。让父亲躺好。强行压着,挽起衣袖,上上下下,左左右右,反复推拿敲打。 那一日,我们推着父亲去逛商场,特地买了过冬过年的棉衣、棉裤。当父亲穿上时,顿觉精神清爽,焕然一新,而那一双黄色皮鞋,父亲试了一下,搁置一边,留作春节穿。 没有人知道,那双父亲终是没能在春节穿上的黄色皮鞋,成了父亲的遗物,我一直珍藏起来。没有人知道,在万籁俱寂的夜里,我会悄悄把它取出,端详,凝视,会把它穿在自己的脚上,轻轻地踩在地板上,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,又几步。 2018年1月6日,我在微信圈里写道:草木的骨骼,泥土的肉身。草木折腰,身陷大地。肉身剥落,散落成尘。我们用一场盛大的仪式送父亲远行,走进时间的虚无里。 办完葬礼,我们还沉浸于一片空茫和恍惚之中。这时,母亲平静地把我们集中在一起。母亲依父亲遗嘱,每人分了一万元。母亲说:“你父亲病了多年,自觉得拖累你们,心中有欠。这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。”母亲又打开一块蓝格手帕,里面有几千元。她说:“这些钱你父亲一直包好放在身上,他让我在他死后发给你们,他说会保佑你们的。” 手捏那散发父亲体温的人民币,我们不约而同抬起头,无声地瞧着厅堂的墙上。父亲正端坐在黑色边框的照片上。此时,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微笑,静静地注视着大家。 现在已是人间四月天。我坐在故乡的窗前,写下山峦青黛,写下绿水长流,写下远墟含烟、燕子回还、以及打湿四月的雨水。我写下一行行文字,寄给多年来只有在梦里回归,永远遥远的父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