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那年那个“五一”节
夏艳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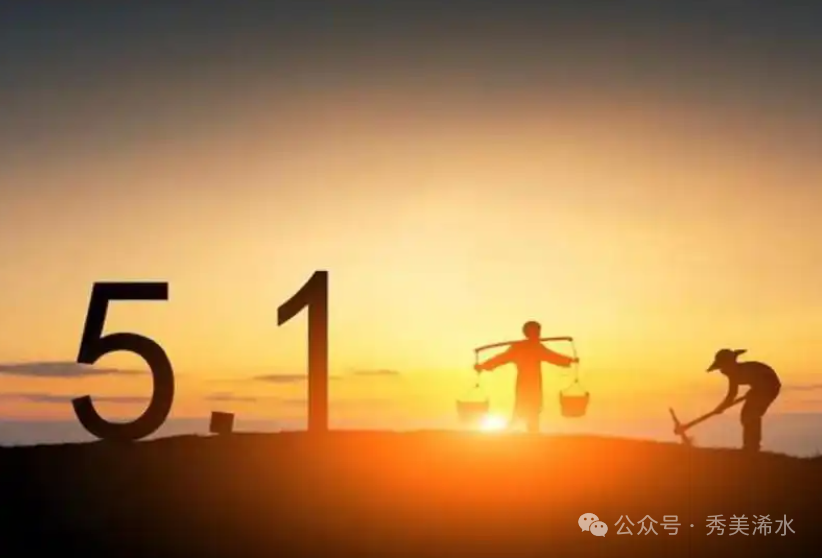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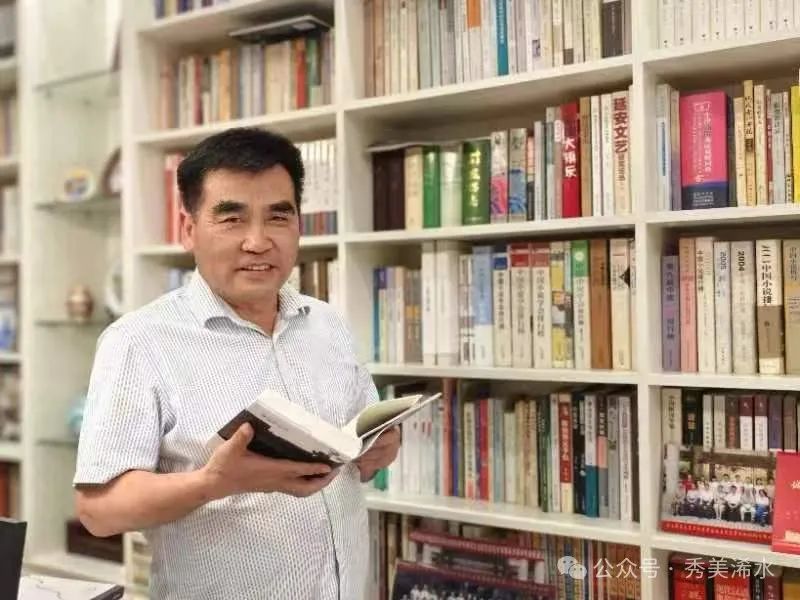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:夏艳平
湖北浠水县人,中国作协会员,在《山花》《长江文艺》《清明》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,有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摘》等转载,并入选多种选本,获全国华语儿童文学铜奖、全国微型小说年度优秀作品奖等20余种奖项,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寻找背景的玻璃》。


那年那个“五一”节
夏艳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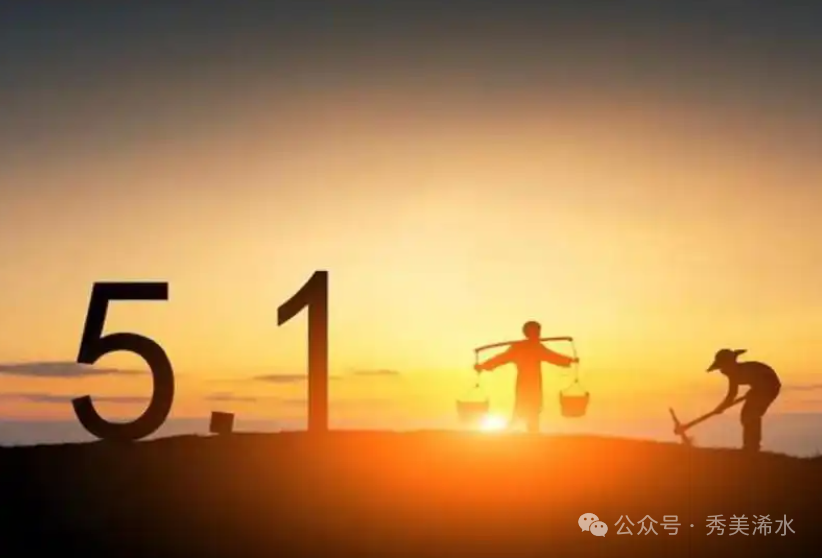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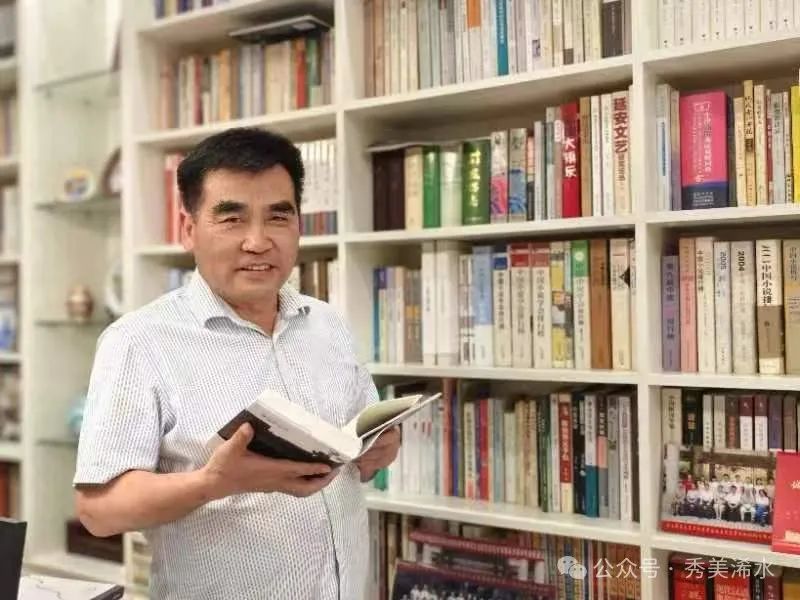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:夏艳平
湖北浠水县人,中国作协会员,在《山花》《长江文艺》《清明》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,有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摘》等转载,并入选多种选本,获全国华语儿童文学铜奖、全国微型小说年度优秀作品奖等20余种奖项,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寻找背景的玻璃》。